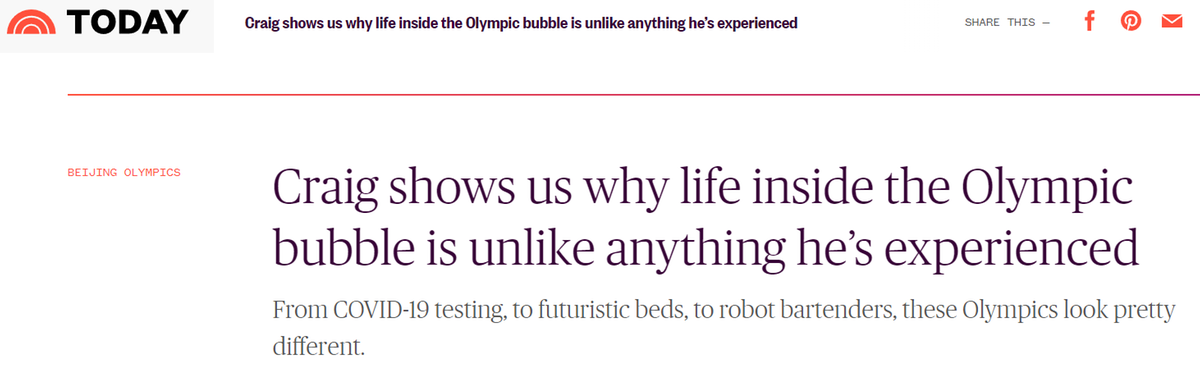人们既期待机器人,也害怕机器人。期待的是,希望机器人能将人彻底解放出来,告别辛苦重复的劳作;害怕的是,如果机器人太过强大,强到统治地球的人类变为屈于机器人之下的奴隶,这是否会带来倒退?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经济学家,有政治家,也有哲学家,还有很多的科幻迷、机器人发烧友,他们都言之有理,无法判断谁对谁错。毕竟,没人能证实未来。
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即便已经如此“智能”,但还是处于非常低的发展阶段。因为机器人诞生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就像人一样,它要成长,要进化。
曹其新教授说,今天一些“机器人杀人”的案例,不过是一些故障带来的机器失灵,还远不到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的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超越人本身的认知,工具理性才会把人异化为物,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技术才会让人走向不归路。
要记得,机器人为人而生,为人服务,这应是永恒不变的逻辑。
人物简介:曹其新,上海交大智能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同时是国家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日本宫崎大学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客座教授。开发过月球漫游车、中型足球机器人(交龙)、管道检测机器人、助行机器人和迎宾机器人等全自主移动机器人,并率领学生在日本大阪举行的1998NHK国际机器人大赛中获得市长奖,连续三年在中国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Robocup足球机器人中型组2对2的项目冠军。同时,还连续三年作为国内唯一被选中参赛队参加了世界杯Robocup机器人大赛。
《机器视觉与应用》曹其新 庄春刚 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是一大特色。接待机器人、物流机器人、递送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巡检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等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惊艳了世界。
对于当今中国人而言,机器人不光是制造业和工业中的担当,也渐渐从生活“奢侈品”变成了“日用品”。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三次浪潮,有关机器人的未来、应用乃至伦理的思考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长江日报“读+”邀请了国家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曹其新谈谈机器人的过去、现在和明天。
让机器人“传承”中医
62岁的曹其新教授造过月球漫游车、中型足球机器人、管道检测机器人、助行机器人和迎宾机器人,最近又在实验室制造一种“中医机器人”。
“自疫情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生命质量,社会需求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其实早在2015年,曹其新就专注于此,所在机构是“生物医学制造与生命质量工程研究所”,他形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个最小单位的“细胞”,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把生物医学往人工智能和集成方面拓展。
他设计的这个“中医机器人”,主要想让其按摩人的脚底反射区实现治疗,这跟普通按摩器有很大不同。“按摩市场鱼龙混杂,一些真正有资质的医生的才能反而发挥不出来。”曹其新设想,这是一个需要用到毫米波雷达、云端大数据、力控算法等的机器人,联网后使用。对他来说,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机器人怎么把中医的精髓学到手呢?
研究了一番,曹其新发现,中医不是靠理论支撑的,本身难以量化,难以用科学解释,能利用的是大量的效果案例和中医积累的经验,而且内部还分成不同学派。曹其新一头钻了进去,跟不同的中医专家打交道,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加入了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相信高手的合力就是‘大数据’,用它来训练机器人,完成网络的识别,就跟训练围棋机器人一个道理。”他认为,这也是对中医的一种“传承”,而且比训练徒弟快多了。
其实,“中医机器人”早已做出成品,但因为机器人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一直在完善当中。“中医强调‘治未病’,并不是一定通过药来治病,我希望中医机器人将来能放在医院、社区中使用,甚至走进人们家中”。
除了男足女足,中国还有“机足”
去年,曹其新教授写了一本教材叫作《机器视觉与应用》。“机器人教材是很难写的,因为它发展太快了,每年都有约30%以上的更新,很多最新的知识可能马上就变成老生常谈。”因此,他平时授课来不及“用教材教”,不可能按照一个既定的框架上课,只能不断修改课件,第一时间不惜“血本”地购买最新设备。
今天人工智能是个很热的话题,但在二十多年前,人工智能处于低谷,机器人该何去何从,大家还不清楚,“机器人本身很枯燥,当初很多学生不愿意读,但是越来越多学生加入进来”。1997年,由国际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了世界杯Robocup机器人大赛,鼓励大家把人工智能技术尝试用在踢赢足球上。
上世纪末,曹其新便带着学生参赛,围绕这一目标培养学生。
曹其新和学生一同造了“足球机器人”。踢得球倒是真实足球大小,但“足球机器人”本身并不像足球运动员,而是一个小车的模样。当时他们用到了视觉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
“现在看来,跟后来这20多年的发展方向是吻合的,我们的预期根本不虚”。
在最早的时候,世界杯只有百来号人参加。“现在不得了啦,疫情期间也有三五千人比赛,而且是不同种类的机器人比赛。还分了青少年组、大学生组。”
中国除了有男足和女足,别忘了咱们中国还有“机足”——机器人足球队。曹其新笑言:“而且中国队在世界上是冠亚军的水平。”
【访谈】
机器人不一定要像“人”
读+:不久前社交媒体流传一个视频,英国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眼睛不仅会眨,还能随人的手指自如转动。现在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很多领域,但人形机器人并不多见,为何有这样的差异?
曹其新:这里面首先存在翻译问题,“机器人”是robot,广义来说,只要是有感知、控制和执行能力,就算是“机器人”,并不是像人类才能叫“机器人”,仿人形叫human robot,还有仿狗仿猫的,中国人叫它机器猫、机器狗,属于“机器人”中的极少数。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还是两样,所以人在考虑问题时也会两样。(英国)那边可以凭兴趣去研究,经费由专门的财团提供,而中国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即便要做,也要先考虑清楚谁来提供经费,做出来还要面临卖给谁的窘境。
这跟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为兴趣而研究。而中国学生目前还是要为生计而研究,这两者区别很大。我好多学生毕业后去了物联网企业,要是去传统机械行业的或者医疗行业,开出来的工资只是物联网企业的一半。有时候我就感到可惜,很多好苗子或者好点子没办法延续下去。
其实即便在发达国家,这种仿人形机器人也不普遍,不是批量化生产的,而只作为一种学术上的前沿探索。在技术上,不是中国做不出来,这并非人工智能水平的问题,而是得充分考虑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平时做机器人,功能做完了,在设计外形时,反而要避免它跟人非常像。试想一下,家里的吸尘器,我非要做成人形的,你敢不敢买?你害不害怕?人在心理上是很难克服这一点的。所以仿人形机器人要是放在市场上卖,反而可以视作是一种设计缺陷。
所以机器人在中国主要是“应用驱动”,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大众化的需求。目前在基层,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中国老龄化问题,包括少子化,还包括劳动力缺失的问题,我们的机器人可能会集中做这些事情。
放眼整个国际市场,只要是跟应用需求有关的技术,中国都能做成白菜价。这是中国的利器,也是中国的软肋。创新还不够,原创还不够,这不是人的问题,是财力的问题。
读+:这是不是说明,要进入机器人制造的新境界还要靠经济发展?
曹其新:就是这样。富起来之后,人就想要更多精神享受,机器人就能往娱乐性方向发展。到时候会有更多机器人替代人做一些重复工作,为人服务,这就是另外一个大的市场了。富起来不光是财力上去,需求更加多样,也意味着有更多创新和探索资本,“应用驱动”的状态就会慢慢改变。在短期内,中国开展研究的主要导向还是以应用解决民生问题。不过,这种导向也可以让研究走得更远。
5G远不只是快,还可以让更多先进机器人进入生活中
读+:在高校二十多年,既做机器人又带学生,二十年间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曹其新:二十多年前,大约是世纪之交那时候,我开设了“机器视觉与应用”这门课,那时候还非常边缘,不像今天这么火爆,一上线马上就被选完了,想选只能“拼手速”。一开始只是三十人的小班课,因为大家还不清楚这门课到底怎么回事,学了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课本科生、研究生都想选,后来不得不分几个班,还得限额。我在高校这二十多年来,很明显感觉到“机器视觉”从“隐学”到“显学”,这和时代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机器人智能水平还比较低,而现在普遍需要用这个技术了。
读+:当时为什么想到开这么冷门的课?
曹其新:我所在得实验室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要“智能”就必须要有感知技术。原来做机器人有两拨人,一拨是学自动化的人做机器人,还有一拨是机械专业的做机器人。那么机械专业就会遇到瓶颈:需要感知,但又搞不清楚“感知”是怎么一回事。开这门课,是希望那些没有信息学科背景的人也能利用视觉传感来做机器人。那么汽车学院里出来的人,就能去研究无人驾驶,去造电动车。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为人服务,把人解放出来,就是要提高它的智能程度,这种智能,类似于人的智能,而且要和人进行交互。我还有一门课也很火,叫“脑与机器人”,这门课面向大一大二没有受到技术框框束缚的学生,文理不限,让他们从不同角度自由探索,没有专业基础的本科生认真学一学期,就能让机器人跳舞、爬楼梯,甚至泡茶。
读+:二十多年前机器人是个什么水平?
曹其新:当时基本只有工业机器人。我在日本留学时,研究农业机器人,什么瓜果精选、秧苗嫁接、草莓拣选之类。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很难看到机器人,顶多能在科技馆见着,它是被当成展示品的,是给人做表演用的。当然了,那时候也不是用不到“机器视觉”,只是那时的视觉应用实在太简单。但今天再看,有些餐厅有机器人在跑,甚至泡咖啡都用到机器人,机器人能识别环境,能送餐。特别是5G出来后,机器人已经非常普及了,生活处处都用到,甚至无感。有些汽车可以监测人的呼吸、心脏甚至脉搏,你察觉不到。近些年快递数量越来越多,但你会觉得物流速度快了很多,那是因为机器人的参与,完全用人工是办不到的。而且这些应用,是在未知环境下工作,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在“非结构环境”下工作。
读+:“结构”“非结构”的概念怎么理解?
曹其新:结构环境就是已知环境,也就是固定位置的环境,像工厂流水线就是典型的结构环境,都是固定的标准化的,不可能多一个或者少一个。但是人的生活场景、家庭场景是“非结构”的,在家中,桌子椅子都可能会移动,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机器人按照编好的程序走就会出问题,它必须非常灵活,能根据环境及时感知,而且大部分是视觉感知,然后作出判断。像送菜机器人,要避开客户,绕开障碍物,送到准确的地点,都要用到视觉,送过的地方不会重复再送,是因为有智能算法。这样就自然而然带动了“机器视觉”的应用。
这一次北京冬奥会上亮相的机器人有很多,比如送菜系统和炒菜机器人,其实我们就做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已经亮相过,但是简化掉了很多,当时我说过,这可能会触发一个产业,果不其然,世博会结束后出现了很多集成机器人餐厅。这次冬奥会使用的滑雪机器人就是交大做的,是用来试滑、测试雪道用的。
读+:就“感知”而言,人的感知大部分是视觉,还有听觉,目前其他感知比如触觉、味觉好像比较难通过机器传递,这些是不是也要陆续攻克?
曹其新:只要解决传感器的问题,就好解决。二十多年前,视觉传感器非常贵,要专用的控制板卡,在传感器中是价格最贵的一种,但你再看二十年后,它成了传感器中价格最便宜的一种。便宜到什么程度?手机里摄像头的传感器,最低的就十几块钱,平时买个USB摄像头只用二三十块钱,从贵族到平民了,我们平时掏出手机,用微信扫个二维码,都用到了机器视觉,买菜的老太太都会用。
现在的手机动不动800万、1000万的“像素”,这么高的像素就涉及计算问题,也就是说,要对摄像头扫到的东西作出判断,需要大量计算。传感器是便宜了,但是计算是另外一个瓶颈问题。像二维码之类的计算,在算法里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只用固定的芯片;而住旅馆时的人脸匹配,需要用到很多很多计算。
当然,现在的计算能把数据放到云端,因为5G出来了,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我们采集来的信号传到云端,计算完后再传过来,所以人到宾馆里,那个摄像头能识别你的信息,不管你有没有化妆,气色怎么样,甚至戴口罩也能识别出来,主要是后端的计算在起作用。
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但中国推出5G了。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很多人以为,5G就是快不快的问题,还有什么优势呢?很多人想不到的,5G远不只是快,它还相当智能。它有后台可以计算,可以配合先进的机器,可以让生活有许多想不到的智能化体验。
机器人离高智能化还很远
读+:机器人往前发展,可能是最让人类担忧的进步,伴随的常常是“机器人有自我意识了怎么办”“人要失业了被淘汰了”“机器人统治世界”“机器人杀人”等伦理思考,这些担忧是否会成真?
曹其新:目前看,这种担忧比较多余,更多的是一种吸引眼球或者炒作出来的东西。以前有新闻说“机器人杀人了”,我一看,其实是一个工业机器人,停在那里修理,完后还没等人确定,电源一开,啪一下一个机械臂过来把人打伤了,就是一个机器失灵的过程,可能是因为供电不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这个机器人是伤人了,但不是因为它有意识才伤人,跟“机器人杀人”差了十万八千里。
任何一项技术都有正反两面,机器人就像核能、火药一样,既有服务人的一面,也有毁灭人类的可能,关键看怎么用。其实那些伦理思考跟“机器人”关系不大,而跟“人工智能”关系很大,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载体。把技术用在交通管理上当然没问题,但美国那边有人研究把人工智能用在军用集成上,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用无人机进行军事行动,这种当然会危害人。就技术本身而言,很多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是做不了,是申请项目时,肯定是要先过伦理审查这一关,关键环节要把控好。
现在很多科幻是基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想象,未来看起来好像非常可怕,好像要回到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好像世界要毁灭了。但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会超越人本身的认知?这个很难说,也许有那样的情况出现,但也非常遥远。
机器人也是要经历进化的,就像人、像地球一样经过历史的变迁、长久的进化。但就目前看,人类实现机器人下围棋,都花费了不小力气,离实现相当高智能的程度,还差了很远很远,目前机器人也只能发展成这样,在视觉上满足我们生活的需求,仅此而已,还处于一个很低的阶段,远不如人类本身那样流畅。尤其我们对人类自身的复杂程度都没了解清楚,让机器人复制也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也许那一天会来临,但不知道是几百年、几万年后去了。或者说,虽然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伦理思考,但是还轮不到现在的我们担忧。更何况,眼下还有好多更需要人类担忧的东西。
 机器人天空-为机器人开发者和爱好者服务
机器人天空-为机器人开发者和爱好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