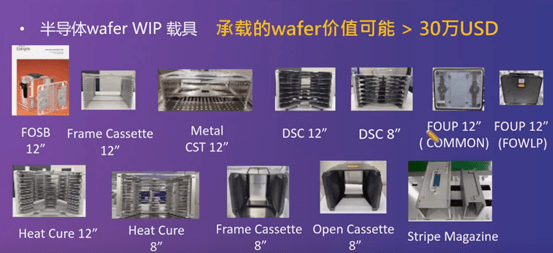机械外骨骼是一种机器人,它是人类的新技术。你应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见过被用于战争的它们,例如《机动战士高达》《环太平洋》里的战斗机甲,或是《钢铁侠》系列中的武装动力服。
但当真正落到我们身边时,机械外骨骼这项科技已显得没这么“科幻”。毕竟它只是做到了一件对人,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行走。对一些人来讲,站立、行走就像一种“神迹”,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却无法企及的目标。外骨骼为他们带来了一个希望,那就是通过行走,将他们从那个小房间带出来,来到那个阳光下的世界。

我们找到了康复外骨骼这项技术的研制者与使用者,试图还原这项“神迹”作用于个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再神奇的科技也只能做到一部分事。站起来之后,那段更长的路,还要他们自己走。
健身房
所有的机器都是“跑步机”
用健身房形容这里更形象些。它有健身房的一切条件:挑高四米的天花板,自由活动的空地,陪同运动的专业人员,次卡制度,以及一排排机器——它们都在和人一起运动。
但这里应该会是那种最安静的健身房。没有快节奏的音乐,没有推举杠铃时的“嘿咻”声,没人挂着毛巾倚着器械谈话。光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白光,而流汗是无声的。
机器在出声。吱呀吱呀的声音在空气里绕,和双脚踩在跑步机上的声音很像,但要慢得多。可这声音的节律精确无比,那是计算机刻定的频率。人,则和机器连接在一起,他们把它穿在身上。这座健身房是一个使用机械外骨骼机器人的康复中心。在这座健身房里,所有的机器都是“跑步机”。
在人类的幻想中,机械外骨骼是那种能把人变成“超人”的机甲。但在这间健身房里,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科幻”或“神奇”搭边的元素,人们只是在外骨骼里行走而已。但行走,或许已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
“健身房”在坐落于北京亦庄的大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内,是这家机器外骨骼制造企业搭建的康复中心。每天,都有数十名下肢行动不便者穿戴上不同型号的机器人进行康复。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是伴生而来的脊髓炎症,有些是事故引发的脊髓损伤或脑性瘫痪。但也有不少共同点。例如男性和青少年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而陪伴前来的基本上全是母亲。
一名康复师告诉记者,到这里进行康复的患者,基本都是因病情过重,在医院或其他机构难以得到有效康复的。在机器里运动的人中,有些人曾会行走,有些人从来不曾。对于截瘫者,身体就像从某一位置“断了电”:截至某条线,大脑的指令不再能继续传下去。而外骨骼机器人,就像一台发电机,通过重复行走,接上那截断电的神经。

邵海鹏在2017年底第一次使用外骨骼机器人,他是这间健身房里运动最久的人。“断电”发生在2017年6月3日。那天,他在建筑工地的钢架上做电焊。上午的活儿就剩最后一块钢板,做完就吃饭。这时,一阵风刮来,他站立不稳,从17米高的平台掉了下去。医学影像显示,邵海鹏的腿骨在加速坠地时被挤碎,其中一片碎骨破坏了脊髓神经。
截瘫。手术加术后恢复总共用了一个月,又去养老院做了三个月康复——因为那里有简单的设备,也便宜,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要是去“正规”的康复中心,一天就得两百多。康复也不顶用,邵海鹏说。就是那么老几样,针灸、烤灯,再有人给你弯弯腿,按按肌肉。这只是维持,让肌肉萎缩得慢一点。双腿还是接不到他的指令,邵海鹏渴望站立。
下肢截瘫的最佳康复期是两年,尤其是六个月或一年以内。邵海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日子一天天重复着推进,不仅神经重生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人的意志也会消磨。2017年底,他的康复师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他告诉邵海鹏,北京有个实验室在研制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在招志愿者。邵海鹏去了。12月,东北已经入冬,他坐车南下。反正是做“小白鼠”,不花钱,试试呗。
发电
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它
健身房里用得最多的机器叫“艾家”,是一款家用康复外骨骼。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支撑用的钢架,两条外骨骼机械腿则固定在架子靠背上。邵海鹏是健身房里少有能独立站上去的人。使用外骨骼康复四年,邵海鹏恢复得不错。外骨骼可以调整机器发力和个人发力的百分比,他现在已经可以仅用自己的力量,带动机器运动了。
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邵海鹏还记得他第一次站进外骨骼时的感觉。最强烈的改变是视野。他形容不好自己站上去那一刻的感受,就觉得“又想哭又想笑”。世界像是一下子往前翻了90度,说话时不再只能看到对方的下巴,炒菜时能看到锅里全部的东西——他终于能做到“平视”这件事了,他又回到那个将近一米八的自己。
站上机器,邵海鹏长高了足足一米。对他来说,这段高差的含义不只是长度。那天以前,他是站在高台上作业的焊工,疫情没来时,甚至还能自己包点工程。他1991年的,快三十了,过两年要成家呢。现在,邵海鹏从床上掉下去都爬不上来。
实验时,邵海鹏上下午要分别使用两种辅助康复工具,上午是最新的外骨骼机器人,下午是一款传统支具——辅助站立床。外骨骼用算法模拟人类行走,但邵海鹏还是适应了一阵。他得重新学习走路。机器人匀速地向前迈,每一步的动作和步程都完全相同。机器为他划定了正规的步态,邵海鹏的腿总是迟滞于机器的步子——他几个月没走过路了,总怕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它”,邵海鹏这样形容。
随着把身体更多地交给机器,邵海鹏也感觉自己正一点点拿回自己的下半身。百分之百,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五十,需要机器的借力越来越少,邵海鹏在出汗,这无疑是快乐的。2018年春节前,历时一个多月的实验结束。在最后的测评中,他发现自己可以把脚从轮椅的踏板上放下去,甚至努努力还能提动微弱的神经把它拉上来。2018年春天,过完年,他联系上了大艾机器人的创始人帅梅:“你那还缺人不?你给我点生活费,我给你当个模特呗?”

邵海鹏已经受不了从机器人上下来,矮下身子挤进那台狭窄的轮椅了。
黑箱
找不到任何能宣泄的对象
每名康复外骨骼的使用者都有过这样一个黑箱。它可以是家庭,是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屋,是与“外面”相对的一切,是在“社会上”没法被公众看到的地方。
帅梅是大艾机器人的创始人。从2009年开始,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系副教授的她开始研究应用于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大艾机器人研制成功,公司进入运营阶段后,帅梅会加进所有的产品推广患者群,去做讲座,推广产品,也听那些残障者的故事。
她开始发现,疾病不仅仅会限制着人体,还缠绕着家庭。在下肢行动障碍者中,一部分人的残障与生俱来。除了患者本人以外,受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母亲。“一些妈妈长期受孩子的折磨,精神状态都是不太正常的,她们会易怒、敏感、挑剔,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她的原罪。如果家庭能为她支撑一点还好,否则她就只能一个人承受一切。”
侯羿朵在那间“小黑屋”住了五年。17岁的暑假,她从家里二层阳台上摔了下去。那场事故导致她双下肢截瘫,那天后,她不再去上学。行走停止后,家庭也暂停运转。为了治疗和康复,父母卖掉了县城的房子,回到了村里老家。
从2009年到2014年,她几乎没离开过那间毛坯房。村里没有年轻人,基本都是带着小孩的老人。有人觉得残疾人“晦气”,她也不出家门,没人说话。水泥地、水泥墙,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电视,这就把小屋塞满了。侯羿朵也不爱出屋,能在床上耗一天。“封闭”“绝望”,她找不到任何能宣泄的对象,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她诉说——她需要的是家庭以外的对象,对于身边人,她知道自己不可以“给他们施加任何压力”了。
网线像是卧床时插在身上的管子,连接上虚拟世界,忘掉现在,成为另一个人。在网上她水贴吧、打游戏,所有的朋友都是网友。虚拟与现实界限分明,没人知道她在“黑箱”里的样貌。侯羿朵基本上一睁眼就扎进网络,“完全沉浸里面,甚至不记得自己生病这回事”。有一次,直到母亲从床上把自己抱下来上厕所,她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意识到“原来我的真实生活是这样子”,一下子痛哭出来,但没过一会儿,就回去“网上冲浪”了。
父亲在外挣钱,母亲照顾孩子,这是许多残障家庭的组织模式。五年后,母女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即使父亲和一些亲戚反对,觉得在家至少能活下来,“一辈子不会饿死”,母亲还是把她从村里带去了长沙,一边打工,一边让她尝试学习自理,走出房间。出走的时候,母亲说:“人活在世上,不能只为了吃口饭而已。”
重生
恨不得24小时穿着它
2014年8月,从小屋奔到长沙,走到更大的社会后,侯羿朵不再躲在门后面了。她第一次在网上查了自己的病,认识了“脊髓损伤”这个名词,还在社交网络认识了不少坐轮椅的朋友,这让她知道世界上并非只她一人无法行走。
那些年轻病友们总能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还能坐轮椅出门。侯羿朵感到一种迫切,她必须得马上走到阳光下面,“公开”并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有新生活。侯羿朵再次真正意义站起来——和那些用双腿行走的人平视,已经是2021年10月,一个朋友介绍她来到一家位于杭州的外骨骼机器人公司体验。
侯羿朵用外骨骼“走”了两圈,十几分钟,再下来时已泪流满面。她感觉下半身又“活了过来”,那是一种“来自健全生活的冲击感”。但这台机器对于侯羿朵来说来得太晚。她已经截瘫12年,加上伤势较重,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会每月都去使用外骨骼,不仅为一种“行走的感受”,多项研究表明,站立对下肢残障者的血液循环、胃肠消化及心理健康都有助益。
邵海鹏无疑是“幸运儿”,他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由两个穿着外骨骼机器人的截瘫者参加的马拉松。为此他从夏天训练到入冬,像位准备上太空的宇航员。马拉松在四座城市举行,每站要持续走十多公里,平均六七个小时。除非工作人员下班,或是小便,否则邵海鹏根本不想从外骨骼里走出来。他恨不得24小时穿着它。
24岁的杨阳是健身房工作人员眼中最熟悉的面孔,8岁的一场车祸导致昏迷醒来的他被诊断为脑瘫。生活从2006年10月开始彻底改变了,从那往后的几乎全部时间,杨阳都与母亲连在一块,父亲在外挣钱。
头三年,杨阳被送到北京博爱医院做康复,每月开销一万五。金钱、情绪、时间,全部在康复中被吸收、湮灭。在那场事故后的十几年里,杨阳的每一天也都像是复制粘贴的:吃饭、睡觉、看电视、打游戏。和侯羿朵一样,杨阳把生命的更多部分投在网络里,还有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
杨阳是2020年10月第一次走上外骨骼的。那段时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位使用大艾机器人康复的男孩,通过私信,联系上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北京试用。这是他第一次不依靠人站起来,紧张、害怕,怕掉下来。那次走了半小时,杨阳全程紧着腰板,不敢低头。他花了几周时间才把自己交给机器。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变化,他会笑了。
从走进健身房踏进外骨骼开始,杨阳似乎开始进入真实的世界,他在现实中的所有朋友都是在这里认识的。在现实中的“重生”需要在吱呀的脚步中实现,杨阳要走出第一步,首先要生活自理,不让妈妈太过操心,让两个人都能过上自己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理想
要走向那个更大的社会
范滔是健身房里恢复得最好的人之一。18岁的暑假,因为在厂里做临时工时的一场事故,他脊髓损伤导致截瘫。用机器人康复半年多,他依次摆脱了轮椅、助行器、拐杖,已经能像十八岁之前那样走一会儿路了。在健身房里,每个人都有相似的背景——不能行走,无法融入外边的世界。人人平等,范滔把这里形容成一个“理想社会”。
健身房为肢体残障者们提供了一个和那个“外边”略有不同的目的地。这里的人可以相互理解处在残障者这个身份当中的感受。范滔有时会开着电动助力车走到街上,他总感觉自己“吸引别人的目光”,那些直立行走的人是一个个移动的“1”,他是唯一把身体“收起来”的人。
邵海鹏在老家也有不少残障者朋友,他平时会打视频过去,一接通,经常要么看到人躺在床上,要么窗帘拉着,背景是黑的。他想把这些朋友拉出来,甚至在视频里活动着“炫耀”自己的双腿,作为一个“榜样”让他们不要就这么放弃康复。但邵海鹏也知道,这些人没有他这样幸运。作为大艾机器人公司的产品宣传者,他可以来到北京,免费使用机器人康复。但县城里的无障碍基础设施配套与大城市差别不小,对于需要依靠轮椅来活动的人们来说,一道几厘米的小坎都会成为把他们拦在屋里的墙。
另外的问题是钱。帅梅称,为了让康复机器人能用于更多的残障者,公司不断研发成本更低的产品,目前最便宜的机器人售价十几万。也可以选择在康复中心使用,价格是一小时300元。但这依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
和人一样,科技也得面对它与社会的关系。北航教授帅梅研发过比外骨骼机器人难得多的技术。读博时,她就帮助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对五轴五联动数控技术——一项对高质量工业加工至关重要的科技的垄断。和那项大工程相比,康复外骨骼就是“造个小机器人”——帅梅这样形容。
但难的是把技术转化为与人更加贴近的“产品”。2003年,帅梅到清华大学担任博士后,转向仿人机器人研究,成功研制出了一款能在崎岖路面上行走的机器人。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后,她了解到康复机器人这一领域。当时,在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外骨骼技术已经从最早的军事应用转向医疗行业,但只是作为一项辅助行走机器,且价格高昂,单价高达数百万人民币。
2009年,帅梅带领实验室里的六七位学生开始研发可以在中国普通百姓中落地的产品。2013年,第一例外骨骼机器人问世,经过一轮轮实验、改进,机器人的运行逐渐趋于稳定,拟人程度越来越高,让使用者能拥有“自主行走”的感觉。
在康复这件事上,外骨骼能做到的也只有一部分。邵海鹏说,对于“我们这些残疾人来说”,即便像他这样,身体已经恢复到不错的程度,也无法抹平自己与社会的距离。范滔和邵海鹏一样,不仅对身体康复的要求越来越高,“坐起来想站,站起来想走,会走了就想跑”,还想要从健身房走“毕业”,走向那个真正的社会。
“残疾人”这个身份还困着他们。“要么就是做个体户,要么就是靠网络”,邵海鹏这样总结残障者们在社会上自立的出路。侯羿朵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两百多万粉丝,在视频里她坐在轮椅上唱歌跳舞,也发布自己用外骨骼机器人的作品。从那间小屋走出后,她留在了长沙生活,现在已经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但在用真实身份走向网络时,她还是会偶尔面对质疑。
现在,邵海鹏想“往前再多走一步”。他的计划是,做一台既能电动又能脚踏的三轮助力车,骑着它环行中国,在徒步中开直播。夏天走北边,冬天走南边。下坡自己走,上坡开电动。“我上坡就是走不上去,咱也不骗人不整那假徒步”。邵海鹏准备离开健身房,走向那个更大的社会了。反正无论上坡下坡,都是在往前走。
 机器人天空-为机器人开发者和爱好者服务
机器人天空-为机器人开发者和爱好者服务